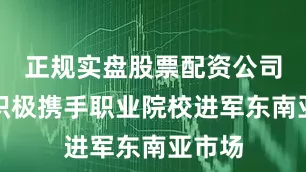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5年第10期读书与传媒栏目
作者:钟振振
世界各国都有美丽的山水。许多国家美丽的山水,仅仅是自然景观,是大自然的恩赐。而中国的山水,既是自然山水,更是人文山水、文学山水、诗化了的山水,几乎找不出一处山水没有经过诗人的吟咏。
图片
图片
古诗词里的山
在古人眼里,最有名的山当推“五岳”。我们就先从五岳讲起。
山东的泰山,东岳——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望岳》诗: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泰山是什么样子?泰山绵延不绝,苍翠了整个山东大地。上天使它聚集了一切神奇与峻秀,它的高大,山南山北仿佛隔开了黄昏与拂晓。远望泰山,云气缭绕,胸中仿佛也有重云生成,激荡。瞪大了眼睛,目送鸟儿归山,直到它们消失在苍茫的山色里,眼眶都快要瞪裂了。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的顶峰,俯视那些个矮小的群山!青年诗人杜甫用最高亢的音调,唱出了他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在写这首诗之前,他参加进士考试,落榜了。但他没有因为挫折而垂头丧气,仍然保持着积极乐观、奋发向上的锐气。尽管他一生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凭着这股锐气,至少在诗歌创作上,他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座文学的“泰山”!
陕西的华山,西岳——明代诗人朱志𡐤《华山》诗中的名句:
三峰秀出云霄外,一掌高擎日月边。
华山三峰——南峰“落雁峰”、东峰“朝阳峰”、西峰“莲花峰”高出云霄之外,华山东峰的奇特景观“仙人掌”,像是高举在太阳和月亮的旁边。两句14个字,写尽了华山的高峻和雄奇。
湖南的衡山,南岳——清代著名诗人魏源《衡岳吟》诗:
恒山如行,岱山如坐。
华山如立,嵩山如卧。
惟有南岳独如飞,朱鸟展翅垂云大。
说北岳恒山像是在走着、东岳泰山像是在坐着、西岳华山像是在站着、中岳嵩山像是在躺着,唯独南岳衡山像是在飞,像红色的大鸟在飞翔,翅膀展开像天边大块的云朵。不但写活了衡山,也对五岳中的其他四岳作出了形象而生动的概括。
山西的恒山,北岳——清代诗人陈培脉《恒山》诗句:
上应天枢象北辰,众山环拱碧嶙峋。
云霞隐见金银阙,昏旦盘旋日月轮。
写恒山对应着天上的北极星,群山都环绕在它的周围。云霞之中,隐隐现出金银装饰的道教宫殿;早晨和黄昏,像车轮一般的太阳和月亮都在它身边盘旋。
河南的嵩山,中岳——宋代诗人邵雍《登封县宇观少室》诗:
群峰拥旌幢,巨石罗剑戟。
日出崖先红,雨馀岚更碧。
远眺嵩山,群峰像是旌旗簇拥,巨大的山石像是罗列着剑戟之类的兵器。太阳出来时,嵩山的山崖首先被曙光映红;下过雨后,山中的雾气显得更绿。
除了“五岳”,中国的名山还有许多。例如:
陕西的终南山,主峰是太白峰——李白《登太白峰》诗的名句:
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
站在太白峰的峰顶上,举起手来几乎能够摸得到月亮;再往前走,仿佛就没有山了。不是真的没有山,而是说和太白峰相比,其他山简直不算个山。杜甫咏泰山,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还承认其他“众山”也是山,只不过小了点而已;李白却连小山是山也不承认,无意之间,透露了他不可一世的气魄。李白的诗,往往精力饱满,境界开阔,气象宏大。这些特点,在他写的山水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是盛唐时期磅礴的时代精神,和他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豪放的审美追求,共同在起作用。
唐代的首都在长安,今天的西安。终南山向东一直延伸到西安的南郊,所以唐诗中写终南山的作品比较多,出色的作品也比较多。再如,唐代著名诗人王维的《终南山》: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
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总写终南山的地理形势。“太乙”是整个终南山的别名,也是终南山主峰的名字。“天都”,双关着天国里神仙世界的都城和人间王朝的都城。它既夸张形容终南山主峰高耸云天,又客观交代它与大唐帝国的都城长安挨得很近。终南山数百里绵延不断,一眼望不到头,仿佛一直延展到海边。“白云”“青霭”,都是山里的云气,因离人远近而有浓淡厚薄的区别。登山前行时,人像刀片划破云层而向上走;回过头来望身后,被划破了的白云重新又合成一片。近看身前,似乎被草木染绿了的云气薄如轻纱;而走进轻纱般的云气,身边的景物又一一呈现,云气淡得好像不复存在。这样的体验,上过高山的人都不陌生,但在王维之前,还没有人能用凝练的诗的语言将它描绘出来过。古人把天上的星空区域和人间的地理区域互相对应,称作“分野”。“分野中峰变”,说终南山的山脊是不同行政大区的分界线。“阴晴众壑殊”,是说终南山沟壑纵横,众多的山谷有的阴有的晴,气候不一致。最后,说想找个有人家的地方过夜,因此隔着涧水向砍柴的樵夫问路。写终南山虽然高深莫测,却不阴森荒凉,山里有村落,有人居住、生活。终南山景致万千,令人舍不得离开的意思,都含蓄地包括在内了。王维不但是诗人,而且还是著名的画家。画家都明白,画山水,如果不点缀一两个人物,就显得呆板,少了一点灵气。结尾有主客二人,隔水问答,富有生活情趣,使得整幅画面都灵动了起来。
新疆的天山、甘肃的祁连山,古代也称天山——李白《关山月》诗: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纯粹是天山的自然风光;而唐代另一位诗人陈羽的《从军行》诗:
横笛闻声不见人,红旗直上天山雪。
还写到了唐军将士冒着严寒行军翻越天山。远远望去,将士们的身影微小得根本看不见。但是,听到那军乐横笛的声音,看到军旗在飘扬,直上天山。冰天雪地一片白,映衬着军旗的那一抹红,就格外耀眼。将士们的英姿虽然没有出现,却给读者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河北的石邑山——唐代诗人韩翃《宿石邑山中》诗:
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苍望转迷。
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
晓月两句都是夸张山的高大:拂晓时的月亮像是在山上的树林里飞,秋夜里天空中的银河,都被隔在山峰的西边了。真有气势。
江西的庐山——宋代著名诗人苏轼的《题西林壁》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横着看,是一道道岭;侧着、竖着看,是一座座峰。远近、高低,各不相同。为什么我们看不清庐山的真实面貌?只因为我们身处在庐山之中。这首诗,借写庐山说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只有跳出事物之外,站在特别的高度,才能真正看清楚事物的全貌和真实面貌。
安徽的天门山——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望天门山》诗: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长江东流,劈开了天门山,使它成了夹着长江的两扇门。诗人乘船向天门山驶去,只见天门山外,遥远的江面上,有一片白帆,正从太阳那边迎面飘来。
重庆地区的山——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九首其九: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这是古代山水诗中,自然山水与当地民俗、当地人民劳动生活结合得最紧密、最完美的作品之一。
诗人选取的山,不是自然的原生态的山,而是经过当地人民辛勤劳动、开发了的山——山坡上种着桃树和李树,春暖花开,满山李白桃红,层层叠叠,像灿烂的云霞。高山上缭绕的白云里,有烟火,有人家。既然有人家,当然就有日常的生活与劳动。手臂上套着成串金手镯,头上插着银钗的女子,带着坛坛罐罐到溪边、江边来提水,背上山去饮用;男人们头上顶着斗笠,腰里挎着长刀,到深山里去开垦荒地,播种谷物。“烧畲”,是放火烧去地面的草木,用长刀划开地面种庄稼。从诗中女子的打扮和男子的装束,可以知道写的是西南的少数民族。祖国的山河,正是由于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用汗水浇灌而大放异彩。
图片
古诗词里的水
大海——汉代曹操《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这首诗,情满于山、意溢于海。最精彩的一段是: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精彩在哪里?它用了一种高妙的写作手法,不对大海作正面的直接描写,而是从侧面、背面迂回曲折地去描写。你看,太阳、月亮的运行,银河星光的灿烂,仿佛都出自大海,那么,海的辽阔无边,包罗万象,岂不尽在其中,还用得着说吗?如果我们一味地从正面直接去写海的大,哪怕你用尽词汇,也不过只写了个“大海真大”;而诗人巧妙地从侧面、背面迂回曲折地去写,就不仅写出了“大海真大”,更向读者展现了日光下镶了金的大海,月光下镀了银的大海,星光下嵌了万千颗钻石的大海,这大海种种面相的一幅幅壮美画卷叠加在一起,就使得诗的审美效果达到了最大化!
海潮——说了海,附带说一说潮。中国有世界三大涌潮奇观之一的浙江钱塘江的中秋大潮。
宋代著名词人周密的《闻鹊喜·吴山观涛》词:
天水碧。染就一江秋色。
鳌戴雪山龙起蛰。快风吹海立。
吴山在今天杭州西湖东南,钱塘江北,是观潮的胜地。潮起之前的钱塘江,满江浅青的颜色,仿佛是秋天的风露染成。突然,海潮倒灌进江里来了。仿佛蛟龙从蛰伏状态中苏醒过来,开始翻江倒海。涌起的潮头好像巨大的海龟顶起了雪山,又好像是大风把海水都吹得站立起来。词人形象地为我们刻画出了钱塘江大潮来时的那种奔逸跳荡的动态之美。
宋代另一位词人潘阆,也有《酒泉子》词:
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又:
弄涛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他夸张说,海潮来时,潮声惊天动地,像是万鼓擂动。海潮的大,令人怀疑大海的水是不是倒空了,都灌进钱塘江里来了。他还记录、描绘了当地勇敢的男青年在潮头冲浪,踩水站立在潮头,手里挥舞着的红旗,并没有被潮水打湿,足见技艺高超。这些,都是画家也画不出来的。
说完海,接下来就该说中华民族的两条母亲河——长江、黄河了。
长江——宋代诗人曾公亮《宿甘露僧舍》诗:
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
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
古往今来,歌咏长江的诗词佳作很多,精品也很多。曾公亮是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学家,曾当过中央朝廷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最高军事长官。他并不以诗著称,但偶一出手,居然惊艳。这首七言绝句,只用了28个字便写活了长江的汹涌澎湃,是文学精品。
“甘露”即甘露寺,在今江苏镇江,长江南岸的北固山上。读者未到北固山,读开头二句,会以为那山千峰万壑,云雾缥缈,满谷苍松。然而到了那里,看到的只是孤零零的一道山冈,高度只有50来米,大失所望,要怪诗人浮夸。但仔细揣摩,才知道这里并不是实写峰峦、山谷和松涛。北固山断崖百尺,像墙壁直立在江边。惊涛拍打山崖,发出轰响,在夜里住宿在山顶寺庙里的诗人听来,可不就像山谷里的松涛在床底悲鸣?江上水气与山中云气是一样的,飘到枕头里来,用仿佛周围便是群山来比拟,也合情合理。后面两句,越写越奇妙了。江涛声响太大,吵得人睡不着觉,索性不睡了,起身来,打开窗户看江景吧。江景什么样?月光下巨浪奔腾,像重重叠叠的银山,一波又一波,拍打着天空。窗户一打开,那浪便像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一样,向诗人扑过来。这拟人化的描写,真令人拍案叫绝!
曾公亮的诗,写的是长江动态的美。下面,这另一首七言绝句,是写长江静态的美。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暮江吟》: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真珠月似弓。
前两句写黄昏,写江中。一道残阳,倒映在水中,诗人不说“映”,说“铺”,为什么?因为“映”字太直,太实,不奇,不妙,缺乏诗意。“铺”字炼得十分精彩,有了它,那“一道残阳”就不再是水中的倒影,竟成了一匹红色的绸缎或一条红色的地毯,横铺在江面上。你说妙不妙?更令人称叹的是,那匹红色的绸缎或地毯,并没有铺满整个江面,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半江碧绿、半江朱红,色条对比鲜明,具有彩版画效果的奇丽景观。后两句写夜,写江上的天空与江畔的野地。农历“九月”,有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寒露”,因此诗人写江畔野地,特意选取了珍珠般的露珠。农历的“初三夜”,特殊的天象是月牙儿,因此诗人写江上的天空,特意选中了它。只说“露似真珠”,自然有江畔野地的花草树木隐含其中。只说“月似弓”,自然有江上天空的星辰云气隐含在外。一首短诗,不能什么都写,要懂得剪裁。总之,这首诗的前半与后半,是不同时间、相同空间的两幅画图,全篇是两幅画图的叠印。前一幅画着重在“色彩”,后一幅画着重在“形状”。然而露是白的,月亮是黄的,并非没有颜色,对于前一幅画中江水的红和碧,是暗暗的衬托。一江流水,也有形状。后一幅画中无数露珠的圆形,一弯新月的弧形,都是几何图形;用不规则线条勾勒出的长江来映带,也显得很灵动。
黄河——李白写黄河的名句最多:
黄河落天走东海。黄河走东溟。黄河西来决昆仑。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
无不气魄宏大,但多不是通篇专门写黄河的。因此,我们这里选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浪淘沙》诗九首其一: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
黄河河道蜿蜒曲折,号称九曲黄河。黄河因为挟带着大量的泥沙,因而呈现为黄色,故称黄河。黄河有不少河段风高浪急。黄河一路流向天涯,汇入大海。这些要素,刘禹锡诗里都抓住了。后面两句,巧妙地用了一个典故。晋代作家张华的《博物志》里有个奇妙的传说:相传天上的银河和大海是连通着的。有个人住在海边,年年农历秋天的八月,有木筏子从海上漂来。这人很好奇,于是便带上干粮,登上木筏去旅游,倒要看看究竟能漂到哪儿。开头的十几天,还能看得到日月星辰。后来就一片混沌,什么也看不到,也分不清白天黑夜了。又过了十几天,到了一个地方,有城郭,有房屋。远远望去,房屋里还有女子在织布。有个男人牵着牛到水边来饮牛,看见这位不速之客,很吃惊,问他是怎么来的。海边人如实相告,并问牵牛人:这是什么地方?牵牛人卖了个关子:您回去,到四川去问一位名叫严君平的人,他会告诉你。海边人结束这趟旅行,还真到四川去找了严君平,原来严君平是一位星相学家,他说某年某月某日夜观天象,看见有客星,也就是流星,冲犯了牵牛星座。一比对,那天正是海边人到达银河的日子。这个典故并不直接与黄河相关。但黄河是通向大海的,因此说沿着黄河也能直上银河,到牛郎织女家里去做客。这传说,这诗,说明我们的古人也是很浪漫,很有文学想象力的。
说了长江、黄河,接下来就轮到湖了。
洞庭湖——唐代著名诗人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诗:
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洞庭湖,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在今湖南、湖北两省间。秋季的南方阴雨连绵,洞庭湖水涨满,与岸齐平。这时望湖,湖面更显得开阔。它涵纳了整个天空,天光及其在湖中的倒影,上下空明。真实的天空与虚幻的倒影,界限泯没,浑然一体了。美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朗费罗在他的著名的诗篇《金色的夕阳》里写道:海,只是另一个天。天,只是另一个海。哪是地,哪是天,眼睛难以分辨。相似的意境,孟浩然只用了“涵虚混太清”五个字,比较起来,更为简洁凝练。更精彩的描写还在后面: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云梦泽是先秦时期长江中游的一个超大型湖泊。后来因为长江、汉水泥沙的淤积,湖面不断萎缩,大部分地区已经干涸,只剩下洞庭湖等一小部分。所以,后世也用“云梦泽”作为洞庭湖的别名。岳阳城,当时岳州(今湖南岳阳市)的州城,在洞庭湖的东岸。历来的诗评家对这两句赞不绝口,称为千古绝唱。乍一看来,十个字中倒有两个现成地名,而且占了六个字的篇幅,诗人只加了“气蒸”“波撼”四字,费力不多,凭什么暴得大名?而仔细琢磨,其中颇有讲究。其一,这两个地名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六个字里, “云”“梦”“泽”“岳”“城”五字,都有艺术形象,都有审美意味。其二,这两个地名虽然是死的,但一加“气蒸”“波撼”四字,便“活”了起来。试想,洞庭湖上,烟波浩渺,水汽蒸腾,是不是充满了勃勃生机?风掀潮水,浪走奔雷,岳阳城似乎也为之摇动,是不是凸现了洞庭湖那强大的生命力度?这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不朽杰作——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大型石雕群。那些石雕,如伏虎、跃马等,多就原石的自然形态,三刀两凿,浮雕线刻,用工极为简省,而无不栩栩如生,浑成大气。孟浩然这两句诗,正有异曲同工之妙。
杭州西湖——宋代大诗人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二首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西湖是中国最美丽的景观湖之一。苏轼是古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最优秀的诗人与最美丽的景观湖相遇,必然擦出最灿烂的火花。苏轼在杭州做过官,公务之余,常游西湖,全面领略了西湖一年四季千变万化的美。起句写题中的“初晴”,第二句写题中的“后雨”。两句是说西湖山好水也好,晴好雨也好;山奇水也奇,晴奇雨也奇。后两句,用中国古代最美丽的女子西施来赞美西湖,写“活”了本来没有生命的湖,真是神来之笔! “西湖”是水, “西子”是人,并非同类,本不可“比”,但两者都是天下的绝美,这就有了“比”的理由;何况“西湖”称“西”, “西子”也称“西”,这就“比”出了语言诙谐的趣味。美人的“美”,是淡妆漂亮,浓妆也漂亮,怎么化妆怎么漂亮。“淡妆”比喻雨天的西湖,雨天的西湖颜色清淡,可不就像美人化了淡妆? “浓抹”比喻晴天的西湖,晴天的西湖颜色浓丽,可不就像美人化了浓妆?因此,“淡妆浓抹总相宜”,也就是“西湖晴雨总相宜”!
画山水,写“形”易,写“神”难。四句小诗,如果句句写“形”,是做加法,增量不增质。苏轼这诗,好在两句写“形”,两句写“神”,是做乘法,不增量而增质,使艺术效果几倍几十倍地往上翻。从此,西湖多了一个别名——“西子湖”。人们对这别名的赞同,正是对这首小诗审美价值最大化的承认。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摘自2025年2月26日《人民政协报》)
新华观察|国际人文交流的新动向
文艺评论|中国网络文学出海的来龙去脉、关键节点与创新机制
法学|新征程我国法治建设和法治改革的总体布局
读书与传媒|读书的“阴晴圆缺”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加杠杆软件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